|
|
马上注册,结交更多好友,享用更多功能,让你轻松玩转社区。
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,没有账号?立即注册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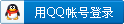
x
1
三年,我要用三年的时间,拥有一座海边的房子。
这是我大学里对朴淳说得最多的一句话。我从小喜欢海,却没有见过真正的海,而朴淳的家在青岛,那个有海的美丽城市。每当我这样说的时候,朴淳就拉着我的手,说,毕业和我回青岛吧,我便说好,大学毕业时我22岁,25岁的时候我们结婚,买一座海边的房子,生两个宝宝,一男一女,每天我带着他们在沙滩上拣贝壳,抓小螃蟹,等你回家,这时候朴淳总是装出流口水的样子笑,好啊,我最爱吃烤螃蟹。我们就是这样在校园的小树林里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重复这段对话,想象夕阳是一只烤熟了的螃蟹。
而毕业很快就来了,朴淳真的在青岛找到一份工作,而我考青岛一所大学的研究生落榜,工作又没有着落,心情一下子像海水退到最低潮。我们开始明白,生活绝不是梦想和诗。
这个时候,安安出现了。他抱着吉他,在酒吧里狂野地唱“我的未来不是梦,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——”。他的歌声和红衬衫,像带着火种一样,点燃了我熄灭的激情。于是,我每天去酒吧听他唱歌,有时在众人诧异的眼光中上台和他一起唱。
一天晚上,安安对我说,我和广州的音乐制作公司签了合约,明天走,他又说,我喜欢你,我想你和我一起去广州,你1米76,我帮你找了一家模特公司。酒吧的客人开始起哄,我情不自禁地点头。
生活象是不可测的沙漠,谁都有可能走失,而爱是惟一的绿洲,只是,并不是谁都能听清爱的呼唤传来的方向。
我没有向朴淳告别,只是留了地址和一封信,信的最后一句是:
我不能做你的诗,正如你不能做我的梦。
2
朴淳不停地给我写信,他写泰戈尔的“抛弃所有的忧伤与疑惑,去追逐那无边的潮水”,写海子的“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”。朴淳不是个谙熟诗歌的人,我可以想象,他花了多少多少时间去找来这许多许多关于海的句子试图打动我,然而,所有关于大海的梦都已经被我遗弃。
我没有给朴淳回信。到广州后不久,我就忙着每个晚上到不同的酒吧去带回烂醉如泥的安安,他为了出唱片灯红酒绿觥酬交错,放任我守着寂寞的睡衣。一开始,我忍耐,再后来,我们争吵,到了最后,连斥责也不再有。
离开安安的夜晚,我到广州刚好一年。我在租来的空荡荡的房间里给朴淳打电话,嘤嘤地哭,絮叨地诉说。索幸,除了房子的回音,还有朴淳给我回应。
很多时候,我们为所欲为,是因为那个等待的人给了自己肆无忌惮的勇气。
我没有答应朴淳回去,失去了安安,我便企图在事业上找回自尊,而朴淳也不多说,只卖掉电脑凑了钱汇给我交模特培训班的学费。
培训结束后,我和一家时装公司签了约,拿可怜的薪水,过清苦的生活,遇到烦心的事便打电话给朴淳,听他安慰。这样的日子一晃又是两年,直到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广告机会被老板的女儿挤了去。江湖险恶,我早已经知道,依然炼不就百毒不侵的神功。在房间里哭得天昏地暗的时候,朴淳像是感应到似的打来电话,一直把我哄到破涕为笑。
晚上猫在床上看《恋之风景》,清淡无味的电影,但看到几米的漫画中天使为了让女孩看到登瀛梨雪,不惜牺牲自己的羽毛时,我的眼泪忍不住滑下来。北村说:“我们大概不会生活,你看,生活被我们弄成了这个样子。但一定有安慰者,来安慰我们的生活。”朴淳,便是我的安慰者,我的守护天使。 我给朴淳写信,问他愿不愿意接受一个一无所有的女孩。
四天后,我收到了朴淳的特快专递,信封里只有一张铅笔画,海浪变成一双张开的手接住一只飞累了的海鸥。
在他眼里,我只是个迷路的孩子。
我赶在新年之前结束了我的合约,退掉了租来的房子,在这个城市飘荡了三年,所有的行李只不过一个箱子。3年了,我在世界兜了一圈,还是回到原点,可是,还能够回到原点,已是幸福。这两个月里我没有和朴淳联系,想给他一个惊喜当作新年礼物,我忘了,总有一天,谁都会经不起等待。
3
我风尘仆仆地站在朴淳家门口的时候,朴淳已经在一个月前被公司派去了北京总部培训,也许回来,也许不。北京和广州,一个最北,一个最南。朴淳是故意的吗?距离那么那么远,远到可以把我忘掉。
朴淳的妈妈方阿姨是个睿智的女子,没有多问,只是用放足了材料的鸡汤诱惑我留下来等朴淳。鸡汤里家的味道,是我这样漂泊多年的女子所无法抗拒的。 只有一个星期便是新年,所有人都忙着晒被褥、置年货,只有我百无聊赖,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兴味索然地看电视。一天方阿姨买年货带回一斤毛线,不由分说拉着教我织毛衣,两针上针,再两针下针,最简单的针法。于是每天早晨吃过早饭后,我就搬了椅子坐在院子里,笨拙地织起毛衣。我在心里默念着“上针,上针,下针,下针”,不明白这么单调反复的动作我如何可以平静地重复下去。冬天的阳光慵懒地照下来,院子里的梧桐静静地立着,邻居家洗净的衣服在风中微微地飘动,我渐渐领悟,每一针把线头从线圈里挑出来,都是一次对生活抽丝剥茧的过程,一针,一针,慢慢平静了我错综复杂的心。我想,或许每个冬天,我都可以为朴淳亲手织一件毛衣。
大年夜朴淳从北京挂来电话,电话里鞭炮的声音震耳欲聋,方阿姨问我要不要和朴淳说话,我摇头,如果两个月后朴淳还会回到青岛,如果两个月后我织好了这件毛衣,我会亲手为他穿上,如果没有,便是缘灭。方阿姨也不逼我,只是对着电话大声地喊:“早点回来,记住家里有人在等你——”,我不知道朴淳有没有听到。
4
第二个月的最后一天,我熬到半夜两点终于织好毛衣,红蓝相间的颜色,一如我期待而忐忑的心。早晨,朴淳的同事打来电话,朴淳在从机场赶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。当时我正在刷牙,穿着睡衣,披头散发,一脸的泡沫星子,听了这话把手机一扔便冲去医院,冲出门,又折回来把毛衣带上。
到病房门口,便听见朴淳和同事的说笑声,同事见我的样子,忍不住笑说:“你怎么不听我说完就把电话扔了,朴淳只是皮外伤。”我也忍不住笑出声,嗔怪他:“你说话不说重点,害我被人看笑话。”而朴淳一直定定地看我,然后拉我到身旁,吻我凌乱如鸟窝的头发,吻我满是牙膏的嘴。
给朴淳换上我织的毛衣接他回家,刚进家门,便收到他订的花,卡片上写着:
我不要做你的诗,也不要你做我的梦,我只要我们真实地拥抱着,一起看海。 |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