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
|
马上注册,结交更多好友,享用更多功能,让你轻松玩转社区。
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,没有账号?立即注册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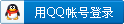
x
历史的轨迹
●马孝义 一、饥饿的童年
大姐出嫁的时候我已经学会了走路。那个极其寒冷的冬天的早晨,父母忙碌着,没有精力来照管我,我只能在客人们吃饭的桌席间穿梭,因为没有资格上桌子,我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客人们低头刨饭,抬头夹菜,那喷香的饭菜实在太诱人了。心里越是急,脚下越是走不稳,数次跌倒后,数次爬起来又哭。母亲把我唤进厨房,舀一碗油汤给我喝了,我用衣袖揩了揩带油的嘴唇,然后一个人缩在温暖的灶台边睡了。送亲的队伍是什么时候走的,我已经完全没有了记忆。
大姐的出嫁,我的身边少了一个依靠,少了一个时常照看我的人。在四壁透风的寒夜里,我着凉了。母亲以为打一碗辣子汤给我吃了就会好的,可是没有凑效,我仍然咳嗽发烧,头脑昏沉,口苦。我向母亲提了一个极为奢侈的要求,我说母亲,我想吃肉。母亲摸了摸我的额头,破例给我煮了一碗滑肉,吃了不到半天,没想到那头昏脑胀的感冒病竟然痊愈。
肉是不常有的,更多的是清汤寡水可以照得见人影的菜叶子稀饭,飘来飘去的几颗米粒,数都数得清楚。菜,下饭的几乎天天顿顿都是那咸得无法进口的泡菜。因为咸,可以少吃,那是父母勤俭持家又无可奈何地选择的唯一的办法。
农业合作社,人哄地皮,地哄肚皮。尽管无数青壮劳力披星戴月早出晚归,但换回来的依然是食不裹腹的日子。青黄不接的四五月间,收工的锣鼓没有敲响,就没有一个社员敢独自回家,挨命一样也只能在地里撑着锄把有气没力地说话。大人没回来,孤单寂寞的我,忍受不住饥肠辘辘的煎熬,常常趴在堂屋的门坎上,一声一声地呼唤母亲,泪水长流。后来累了,就睡了,直到母亲回来,把饿得四肢无力的我抱到床上。
厨房里传来了母亲拉风箱的响声,也飘来了柴禾燃烧后炊烟淡淡的香气。尔后,有了揭锅盖的声音,有了拿碗拿筷的声音,不要人喊,我就慢慢梭下床,来到饭桌边,等母亲端饭来。尽管还是那种清得不能再清的稀饭,咸得不能再咸的泡菜,吃起来,却香喷无比。
但在母亲的碗里,我只看见菜叶和米汤。
这样的日子天天地过,几乎没有什么好转。在家里最困难的时候,我吃过苕藤,吃过野菜,吃过米糠。霉烂的红苕,用清水煮后晾干,然后磨成细粉,放点糖精,和水搅后,捏成面团,在锅里一蒸,端出来,还算好食。
海椒树的嫩叶子,味苦,但摘下来用水清煮,除去部分苦味,挤干水分,放点盐在锅里一炒,那可是再好不过的下饭菜。
大麦收割后,甚至还来不及晒干,就和着苕渣在锅里炕熟,把黄黄的大麦颗粒和苕渣磨成面粉后,抓两三把在锅里,可以搅成一大盆糊糊,一人一碗,吃后把碗底都会添得一干二净。
夏天大雨过后,坡上的地衣被雨水泡胀,一个上午,就可拾得满满的一篮子,提回家来清洗干净,切点泡菜,即使不放油,焖煮出来,也可称得上美味佳肴。
记忆中的童年,吃不饱的日子占多数,吃得好的时候也只有逢年过节,但那是少而又少的,就像清汤寡水中的米粒,那种日子数都数得清楚。
二、缺衣的少年
我的少年处于使用布票的年代。与此同时,也使用粮票,粮票有地方粮票和全国粮票。
我穿过“疙瘩布”。那是用棉花纺成细线,然后通过私人作坊织成布匹,这种布粗糙而厚实,疙瘩翻天的,所以我们称它“疙瘩布”。
我的母亲可以算得上民间的剪裁高手,鞋帽衣裤均能自己缝制,一家九口,母亲只用一把尺子和一把剪刀,就包揽了全家的裁剪。一颗针一根线,又包揽了全家的缝制。
为节省布料,我们的衣裤从来都没有缝制过荷包,其实想来缝起也没有多少作用,因为究竟没有什么东西可装。
一件衣服要穿多少年,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,总之是大的穿不得了小的接着穿,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。” 有时穿得疤上重疤,已经不见了衣服的原形,但还在穿,只是穿在里面。
更要命的是到了热天,放了暑假,我父亲要求我和两个弟弟连裤子都不穿,直接打光胯,他说细娃儿怕啥子,哪晓得啥子羞丑嘛。他的理由是,穿起来不仅热,而且是一种浪费。我那两个四五岁的弟弟倒是很听话,“你说啷个就啷个”,不板不犟的。但我却有些害羞,至多在屋里把衣服脱光,出门无论如何都要穿条裤子。
我们是没有短裤的,即使冬天穿条棉裤,里头也是挂的“空档”。寒风有时从裤脚处往上灌,裆内还是比较冷的。但比起只穿一条单裤来,已经抗寒多了。晚上睡觉,常常“和身滚”,不敢脱衣,因为初初上床,席子冰凉,会冻得人周身起鸡皮疙瘩。
皮带是后来才见到的,当时我们都是捆根鸡肠带,打个活结,通常又忘记了把剩余的一截塞进裤腰,往往就吊在裆前,像风中的一根干缸豆,走起路来甩一甩的。这种鸡肠带也有一定的好处,即使疯架挣断了,扯下来打个疙瘩照样捆,一直捆到后来短得围不住腰杆了,搓根谷草索索也可对付几天。但捆鸡肠带也有缺点,因为不小心就打成了死结,屎尿胀了,搞半天解不开,弄不好就屙在裤裆里。
一年四季,只有隆冬时节才穿鞋子,其余时间,都是打双光脚板。即使穿鞋,也没有袜子穿,所以那时脚上常常长冻疮,起初发痒,红肿,破皮,流黄水,然后化脓,肉皮子粘在鞋子上,扯都扯不脱,这个过程一直要持续到第二年的春天。
冬天下大雾,打白头霜,早晨从床上爬起来就要到坡上拾野粪,经常弄得满头雾水,湿淋淋的。母亲看不过去,就用毛蓝布给我缝制了一顶帽子,那帽子左右两边各有一块“搭搭”,垮下来,可以遮住耳朵。但坐在教室里就不行了,因为老师讲课影响听力,不得不把遮耳朵的两块“搭搭”捋上去。霜风吹进教室,依然把耳朵吹得通红。
少年缺少衣穿,一是家里穷,扯不起更多的布;二是布票供应紧张,即使有钱,也只能干瞪眼。或者还有更多的原因吧。总而言之,我的少年时代没有穿过几件像样的新衣服,穿得更多的是哥哥姐姐们无法再穿的半新半旧或者疤上重疤的“二手货”,尽管如此,也并没感到有什么不好意思,因为那个年代的农村少年,都是这样走过来的。
三、住楼的青年
我一直在农村长大,住的是茅屋和瓦房,不仅低矮狭窄,光线暗淡,更苦恼的是下雨天,通常是大落大漏,小落小漏。至于楼房,小时候连概念都没有,到得十多岁后去过一趟县城,才晓得所谓楼房,至少是是两层以上。砖瓦结构也罢,石木结构也好。
我20岁参加工作,没想到21岁就住进了楼房,那是单位修建的教师宿舍,50来个平米,虽然不宽,却配套功能俱全:一室一厅一厨一卫,还有一个阳台。这个房子我只住了一年,就结婚了,婚后我住妻子单位的房屋,也是楼房。
结婚三年后,我和妻子的工作都有了调动,到了新的地方,楼房更加高级,不仅是磨石地面,而且厨房和卫生间还用瓷砖贴了墙面,有了灰尘,一张湿帕子一抹,光鲜依旧。
再过了四年,我和妻子又调进了县城,因为双方单位都没有现成的房屋供我们居住,只好自己花钱在外面租住了两年。靠着两人的工资,也靠着我们的勤俭节约,手边就有了点积蓄,也就谋划着在城市的中心地带买了一套商品房,100多个平米,朝向也好,光线也亮。我们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,按当时最流行的装修,把一个小家装得很是亮丽,完全跟得上当时的形势。
事物发展变化之快,可谓迅雷不及掩耳。转瞬间,我所居住的这个小县城有了扩城的构想,新的行政中心向涪江北岸转移,在广袤的土地上重新崛起一座新城。当时的政策是鼓励单位职工集资建房,在政策上有些优惠。好钢安在刀口上,我们倾其所有,在妻子的单位上预订了一套250平米的跃层式电梯房,我们的想法是,将来房屋建成后,把双方的父母接来,一家老少住在一起,既可让老人们享受天伦之乐,也可尽到我们的一份孝心。
这种想法,令我们的兄弟姐妹大为感动,他们说我和妻子两人都是拿固定工资吃饭的人,不像他们做生意的钱来得那样快捷,于是兄弟姐妹几个人私下一合计,由大哥出面,将16万元现金送到我手中,叮嘱我把房屋装好点,他们逢年过节回来,就把我这里当作他们的家。至于钱,什么时候有了就什么时候还他们。
亲情之浓,可见一斑。用他们那笔钱,我把那套宽大的住房装得富丽堂皇,父母住进来好久,一直都处在兴奋状态之中,长时间睡不着觉。昔日的“楼上楼下,电灯电话”的幸福憧憬,没想到居然来得那么快,来得那么突然。
有了父母住在家中,我和妻子不再为生活上的锁事担心,柴米油盐酱醋茶,父母亲比我们还想得周到,我和妻子每天下班回家,早已是热菜热饭端上了桌子,饭后连碗都不让我们洗一个,他们很是体谅,说年青人事业心强,工作忙,在单位上班累了,回家轻松一下是应该的。
如今我们一家五口,三代人同吃同住,温馨之家,其乐融融,幸福的生活就像花儿一样开花开朵,做梦都笑醒了。
四、买车的中年
人到中年,腿脚已不如年少时候那样灵便,长期坐办公室,身体少了锻炼,稍微用点体力,就有力不从心的感觉。越是如此,越是不想运动。
人是个贱皮子,无车坐的时候,走路是常事,可一旦公交车出租车多起来,两条腿就再也不想挪动了。住家与单位的距离,步行也不过30多分钟,按理,上下班走一走路,那是再好不过的,然而,人的惰性一经形成,其毛病就很难改变,所以,常常是一出门,就对直走到公交车的站点,车子一拢,抬脚就上,到得单位,一屁股坐在沙发上,半天不挪位,下了班,如出一辙地赶回家。如是经年,少了些日晒雨淋,渐渐地,就养得白白胖胖,脑满肠肥了。
公交车站点多,走走停停,有时嫌那“蜗牛”太慢,出门一招手,就有出租车靠拢来,有的司机还会伸手打开车门,恭请你上座,然后一溜烟跑起来,眨眼就到了目的地,好不方便。
前几年,高速公路和快速铁路开通后,到达主城区的时间大为缩短,以前几个小时的车程,现在个把小时就到了。我的几个兄弟姐妹都在重庆,往往那头煮饭,这头我才开始动身,在车上几句龙门阵都还没摆够,就拢了他们的家。团聚在一起吃顿饭,该说的说了,该交待的交待了,尽管他们挽留着不让我走,但因为第二天要上班,不得不央求他们用车把我送回家。
兄弟姐妹几人,他们的经济比我宽裕,早已有了自己的私车,出门上下都是以车代步。数年前妻子就要求我去学车,而我生性胆小,总认为驾车危险,以至于现在摩托车都不会骑,在妻子面前怕丢脸,我就以一是没时间学车二是没钱买车为由拒绝。其实妻子哪有看不透我的心思的,看看要我学车实在没有什么指望了。“求人不如求己。”她就自己进了驾校,数月后拿回了驾驶执照。一回来,她就把那个本本在我面前晃一晃的,说今后她想去哪能里就去哪里,一不看我脸色行事二不征求我的意见。她还说,心情好可以带我出去,心情不好门都没得,那得意之情溢于言表。
有驾照没车开,妻子心头像猫抓,做梦都想着买车。在我看来,买车是迟早的事情,因为近年来工资直线上升,我和妻子的收入大为提高。即使凑不出那样多的现钱,借点钱交首付,然后在银行搞按揭是可行的。我的想法一说出,妻子举双手赞成。说干就干,第二天她就到重庆提了个车回来。
新手开车瘾大,尽管她上班比我还近,却坚持去来都要开车,给人一种洋昏了的感觉。鉴于我在买车上给予她的支持,没给她打乱石头,所以,她也义务接我上下班,让我感觉心里稍微有些平衡。
开了一段时间的车后,妻子主动收我做徒弟。在诺大的广场上,我把车子开得打抱鸡母旋旋,开是开得走,就是技求水平不好说。我历来对机械的东西不感兴趣,十天半月下来,不仅没有长进,反而有退化的现象,“一山不藏二虎”我说,“我学会了,你就失业了,不好。”其主要目的是,有她开,我落得轻松。
现在车子依然是妻子在开,其实她的技术据我看来,比起那些资深驾驶员来显得很是一般,所以,我经常坐在副驾驶位置上,不时给她提个醒:看倒起,前面有个鸡,鸡前面有个鹅,鹅前面还有一个想过马路的老太婆。注意了,车开慢点,不要慌。
“少啰嗦,我怕还不敌你了!”
“不啰嗦,前天我下车后,去和一个挤眉弄眼的女娃儿搭白,你吃飞醋,连车都忘记了锁!”
夫妻二人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的开车前行,近两年也还走了些地方。玩得开心,过得愉快。 |
|